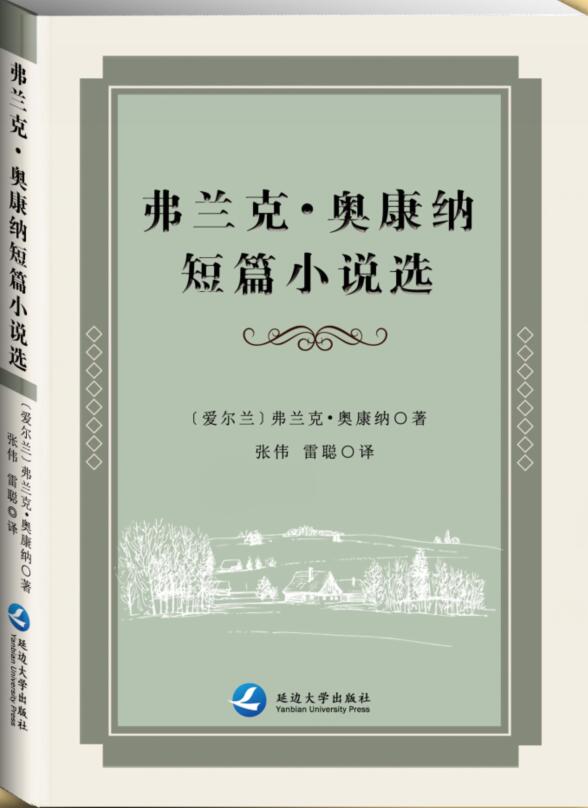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选/张伟, 雷聪译 . -- 延
吉 :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88-2726-3
Ⅰ. ①弗… Ⅱ. ①张… ②雷… Ⅲ.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爱尔兰-现代 Ⅳ.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8290号
目录
树林里的孩子1
一家之主18
醉 汉30
圣诞节早晨43
觊觎者52
世俗之人66
魔法师的学徒75
俄狄浦斯的辩护律师89
未经批准的路线104
预期寿命118
一个借来主题的一组变奏曲136
美国妻子169
不可能的婚姻184
我的俄狄浦斯情结200
怜 悯214
第一次忏悔226
父母的罗曼史236
天 才251
公爵的孩子们265
理想主义者279
新婚之夜292
国家客人301
树林里的孩子
一
每当格雷夫人让泰瑞穿上他最好的长裤和运动衫时,他知道肯定是阿姨要来看他了。她不经常来,但是每次她来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泰瑞的妈妈已经去世,他和格雷夫人,她的儿子比利住在一起。格雷夫人是一个举止粗鲁、爱唠叨、耳朵有点背的老太太,被风湿病折磨得直不起身,她一看见你非得打你一下不可,但是比利人还不错。
这个有点特别的星期天早晨,比利一边急着刮下巴上的胡子,一边咒骂该死的破剃须刀,钟声响彻山谷,提醒人们去做弥撒,这时候,泰瑞的阿姨来了。她急切地走进黑暗的小屋,一张大脸被阳光烤成了玫瑰色,她伸出手打招呼。
“嗨,比利,”她大声地笑着说,“又迟到了?”
“别——管——我,康纳斯小姐,”比利说起话来有些结巴,他从镜子前转过满是皂沫的脸,“妈妈一定偷偷地用剃须刀剃过头发了。”
“格雷夫人好吗?”泰瑞的阿姨大声喊道,她亲了老太太一下,然后,她手忙脚乱地去摸背包的带子。任何关于阿姨的事都令人激动、兴奋,她说起话来又急又快,有时候让人觉得语无伦次。
“快来看,我给你们带了很多东西……不,这些香烟是给比利的。”
(“上帝保佑,康纳斯小姐,”比利说。)“——这个给你,还有一些东西晚餐再吃。”
“你给我带的什么,阿姨?”泰瑞问。
“噢,泰瑞,”她惊慌失措地说,“我忘记你那份了。”
“你没有吧。”
“我真的忘了,泰瑞,”她可怜巴巴地说,“我发誓我忘记了。是吗?有只小鸟告诉我一件事。你猜他说了什么?”
“是什么鸟?”泰瑞问,“鸫吗?”
“一只大个的灰白颜色的家伙?”
“对了,是那只老鸫。他在我们后院唱歌。”
“你猜他让我给你带什么来?”
“一条船。”泰瑞大声叫起来。
没错,是一条船。
吃完晚饭,他们两个去树林里散步。阿姨迈着长长的、轻快的步子,泰瑞差点儿跟不上,然而,她是个很好的伙伴,泰瑞希望她能多来几次。当她真的来看泰瑞的时候,他竭力表现得像个大人。整整一个早晨,他不停地提醒自己:“泰瑞,记住,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已经九岁,你知道的。”当然,他不是九岁,他仍然只是五岁,但是,他喜欢假装自己是女朋友佛罗里的年龄,她刚好九岁。当你到了九岁,你会知道世上的一切。可是,泰瑞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他们到了山顶,阿姨在地上躺下来,膝盖悬在空中,头枕在两只手上。她喜欢这样沉醉在大自然中;她喜欢散步;她总是光着小腿;她经常穿一件花呢子短裙和套头毛衣。今天,她戴了一副黑色墨镜。泰瑞透过镜片只看到周围漆黑一片;山谷另一边的小山丘丛林茂密,汽车和公车在山峦间缓慢地爬行,再远一点,山脚下是火车铁轨和河流。她答应泰瑞下次来一定买一副小的给他戴,一想到要等这么长时间,他几乎不能忍受。
“阿姨,你什么时候再来啊?”他问,“下星期天吗?”
“我可能会来吧,”她说,她晃动着肚皮,用两只手撑起头,嘴里含着一根稻草,冲他笑笑,“为什么?你喜欢我来吗?”
“我喜欢。”
“泰瑞,你愿意搬来和我住在一起吗?”
“哦,好,我愿意。”
“你确定吗?”她半是取笑地说道,“你确定没有格雷夫人,比利和佛罗里陪着,你不感到孤单吗?”
“阿姨,说实话,我不会,”他紧张地说,“你什么时候带我走?”
“我还不知道,”她说,“可能比你想象得要早。”
“你要带我去哪里?城镇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去哪里,”她靠近泰瑞,小声地说,“你能发毒誓不告诉任何人吗?”
“我能。”
“甚至不对佛罗里说?”
“甚至不对佛罗里说。”
“否则,你就得死?”她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否则,我就得死。”
“好的,有一个英国来的好男人想娶我,让我跟他回去。当然,我说我不能丢下你,他说可以带你一起去……那样不是很美好吗?”她说完,拍起手来。
“很美好,”泰瑞说,他也跟着拍手,“英国在哪里?”
“噢,很远,很远,”她说着,手指向山谷,“在铁路的尽头。我们得坐一条大船去那边。”
“哇塞!”泰瑞说,他模仿着比利的语气,当超乎想象的事情发生时,比利就是这么说的,泰瑞已经习以为常。他怕阿姨会像格雷夫人那样打他,但她只是冲他微微一笑。“阿姨,英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继续问道。
“哦,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阿姨热情地大声说,“我们三个会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房子里有电灯,可以随时开关,水龙头里有热水,每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送你去学校。”
“我会有自己的自行车吗?”泰瑞疑惑地问道。
“你会有,泰瑞,一辆两轮的自行车。如果天气像今天这么好,我们就去公园坐坐——你知道的,比利工作的大房子有一个花园,公园里面有树啊,花啊,中间还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在水上划船。”
“那么,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公园吗?”
“不是我们自己的,其他人也会去,还有一些男孩和女孩,你可以跟他们玩耍。你在水上放小船,我念书给你听,然后,我们回家喝茶,我给你洗澡,睡觉之前给你讲个故事。这样不是很棒吗,泰瑞?”
“你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呢?”他小心翼翼地问,“现在讲一个吧。”
然后,她摘下黑色墨镜,蜷缩起膝盖,给他讲“三只熊”的故事,她是那么地投入以至于手舞足蹈起来,她的头发披散着,遮住眼睛,她吼啊,哭啊,慢慢地在地上爬啊,一直到泰瑞半是害怕半是满足地大喊大叫起来。她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伙伴。
二
第二天,佛罗里来小屋找泰瑞。佛罗里住在乡下,因此,她要来看他必须走一里多路,穿过一片小树林,但是她很高兴见到他,格雷夫人鼓励她这么做。她称佛罗里为“年轻的淑女”,佛罗里高兴地脸红起来。佛罗里和科兰斯小姐住在邮局,她对人友好、亲切,大家都这么认为。她身材修长、苗条,头发又黑又亮,脸型稍长,皮肤白皙,长着一个鹰钩鼻。
“泰瑞!”格雷夫人大声喊道,“你的年轻淑女来看你了,”泰瑞拿着他新得到的玩具船从小屋后面冲出来。
“你从哪里拿的这个东西,泰瑞?”佛罗里问,她一看到小船眼睛就瞪得大大的。
“我阿姨,”泰瑞说,“这个船不是很棒吗?”
“我想还可以吧,”佛罗里说,她笑了笑,牙齿都露出来了,好像在暗示,她觉得泰瑞把一只玩具船当成宝贝很幼稚。
唉,这是佛罗里一个很大的弱点,泰瑞觉得很遗憾,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她。她温柔,大方,总是站在他这边,支持他;她讲的恐怖故事那么好以至于把自己吓得不敢一个人穿过小树林回家,但是她好嫉妒。每次她有什么东西,即使只是一个碎布缝的玩具娃娃,她也能把它当成世界上七大奇迹之一,然而,假如别人有点什么,不管多么值钱,她都假装不感兴趣。这一次又是这样。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大房子买一便士的醋栗?”她问。
“我们还是先拿着小船去河边,”泰瑞坚持说,他知道只要他愿意,总能不用理会佛罗里的愿望。
“但是,这些是很好吃的醋栗啊,”她热心地说,好像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吃得到醋栗,“它们有这么大。科兰斯小姐给了我一便士。”
“我们先去河边,”泰瑞吵吵道,“哦,你等会儿看我划船吧——呵呵!”
当泰瑞任性、固执己见的时候,她总是让步,这一次她又退让了;而每一次让步,她总会抱怨一番,这一次也不例外。她说,可能太晚了;他们的朋友杰瑞,那个园艺帮手,可能已经走掉了;斯科特先生,园艺包工头,只会给他们一把不太熟的醋栗。她这点很烦人,总是唠唠叨叨,杞人忧天。
他们一到河堤,便扎起衣服走到水里。河水较深,河流穿过树林,清澈见底,河底铺满了褐色、光滑、圆形的小石头。水流湍急,小帆船在水面上浮浮沉沉,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最后被困在岸边。佛罗里比泰瑞更早对划船失去兴趣。她坐在河边,把手垫在屁股下边,脚趾头在河面划拉着,她看着这条小船,心里失望极了。
“天呐,真不值得为这条小船失去一便士的醋栗。”她恨恨地说。
“怎么了?”泰瑞愤愤不平地问,“这是一条很棒的船。”
“我想它不能正常划行。”她带着指责的口气,一本正经地说。
“水流那么快,怎么可能啊?”泰瑞大声喊道。
“这真是一条很棒的船。”她假装很开心,像个大人似的反驳道,“这可是我头一次听说对船来说水流会太快。”佛罗里这点也很讨人厌——自以为是,似乎只有她知道的才是真理,“这只是一条便宜的小破船。”
“这不是一条便宜的小破船。”泰瑞生气地哭起来,“这是阿姨送我的。”
“她从来不会给任何人任何东西,除了又便宜又破的玩意儿。”佛罗里冷静地说,她说话的语气总是能惹恼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这是她在工作的商店按成本价买的,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你嫉妒。”他大声喊,像村里的孩子们一样,当他们被佛罗里目空一切的做派激怒时,就会嘲笑她。
“这倒是个像样的理由。”她平静地说,然而,她那张瘦长脸仍挂着一副玩笑的神情,“我想你现在就说说,我嫉妒你什么了?”
“因为阿姨会给我带东西,可是没有人给你带任何东西。”
“她很喜欢你。”佛罗里讽刺地说。
“她很喜欢我。”
“我想她不会带你和她一起生活。”
“她会的。”泰瑞说,在愤怒和急于占上风的情况下,他忘记了自己的承诺。
“她会的,我听到了。”佛罗里打趣道,“谁告诉你的?”
“我阿姨。”
“不要把她的话当真,小屁孩。”佛罗里严肃地说,“她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她母亲不会让你和她一起住的。”
“好吧,她以后不会和她母亲住在一起了。”泰瑞说,知道自己终于扳回了一局。“她快要结婚了。”
“她要和谁结婚?”佛罗里漫不经心地问,但是,泰瑞能看出来她很想知道。
“一个住在英国的男人,而且,我要和他们一起生活,就在那里!”
“在英国?”佛罗里重复道。泰瑞知道这次真正把她击败了。没有谁会带佛罗里去英国,她妒忌得发疯,“我想你会去吧?”她酸溜溜地问道。
“我会去的。”泰瑞说,欣喜若狂地看着她屈服,没有人要带这位爱装腔作势的淑女去英国,“我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她告诉你的吗?”佛罗里问,带着怨恨和蔑视的语气,这让泰瑞更加恼怒。
“她会的,她会的。”他疯了似的,大声喊起来。
“哦,她只是在愚弄你,小屁孩。”她傲慢地说,一边用两条长腿拍打着河水,一边继续用那双深邃、邪恶的大眼睛盯着他,像极了故事书里的女巫,“那么,她为什么会把你送到这里来?”
“她没有。”泰瑞说,俯下身朝她脸上泼水。
“但是,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她不慌不忙地说,只是稍微转过脸躲开了水花,“她假装是你阿姨,但是我们都知道她是你妈妈。”
“她不是。”泰瑞尖叫起来,“我妈妈已经死了。”
“哦,他们总是这样告诉你。”佛罗里静静地回答,“他们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但是我知道这都是谎言。你妈妈根本没有死,小可怜。她和一个男人惹了麻烦,她母亲就让她把你送到这里,为了摆脱你。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
“上帝会杀了你,卑鄙的骗子,佛罗里·克兰西。”他说着往她身上扑过去,用他胖乎乎的小拳头不停地打她。但是他力气小,她只稍微用力就把他推到了一边。她在长满草的岸边站起来,满面红光,洋洋得意,假装把裙子的前摆弄平。
“不要再骗你自己了,你是不可能去英国的,小可怜。”她得意地说,“当然,谁想要你呢?耶稣知道,我真为你感到难过。”她假装同情地继续说,“我会为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是你一点儿都不领情。”
然后,她朝着树林的方向跑去,时不时地回头,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他瞪着她,歇斯底里地叫喊。他完全听不懂她说了什么,但是他觉得她终究占了上风。“这个只有九岁却残忍的坏家伙!讨厌鬼!”他说着,一路上啜泣着穿过树林。他知道,她说了谎,上帝会杀了她。如果上帝没有,格雷夫人也会这样做。格雷夫人正在绳索上晾衣服,她酸溜溜地看了他一眼。
“你有什么之前没有的烦恼吗?”她问。
“佛罗里·克兰西撒谎。”他尖叫起来,气得脸色发青,“她是个坏家伙!”
“你又和佛罗里吵架啦!”格雷夫人说,“看看你的伤口,来,到这儿来,让我把你的鼻涕擦擦。”
“她说我阿姨不是我阿姨。”他哭了起来。
“她说什么?”格雷夫人疑惑地问。
“她说我阿姨是我妈妈——送我小船的阿姨。”他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啊。”格雷夫人冷冷地说,“下次看到她来,我一定把她抓起来,用火烤她的屁股,这是她应受的。这个小流浪汉!不管你妈妈做了什么,她都是一个正派的女人,但是谁知道你妈妈是谁,来自哪里呢?”
三
不管怎样,对泰瑞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非常糟糕!吵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一个只有五岁,住在村子一里外的小男孩,又是另一回事。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除了穿过一条人行桥到小火车站。在这条大路上,你可能一星期都见不到一个小孩子。他很想和佛罗里和好,但是她知道她做错了事,格雷夫人正等着她,想追究到底。
更糟糕的是,阿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看他了。她来的时候,有点出人意料,泰瑞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换了一套衣服,因为有一辆汽车正在车站等他们。这辆汽车弥补了泰瑞之前所有的失望(他从来没有坐过汽车)。更让他兴奋的是,他们要一起去海边,阿姨给他买了崭新的铲子和铁锹。
他们从小木桥上过河,在车站的院子里,停着一辆时髦的灰色汽车,车旁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泰瑞从来没有见过他。他看起来也很时髦,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风度翩翩。但是,一开始,泰瑞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他太喜欢那辆汽车了。
“这是沃克先生,泰瑞。”阿姨大声喊道,“快和他友好地握个手。”
“你好吗,先生?”泰瑞说。
“这个小家伙是很受欢迎的拳击手吧。”沃克先生大声说,假装被他吓到的样子,“你会打拳击吗,小参孙?”他问。
“我不会,”泰瑞说,匆忙跑到车后面,爬上了车。 “嗨,先生,我们会穿过这个村庄吗?”他又问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从这个村子穿过呢?”沃克先生问。
“他想炫耀一下。”阿姨“咯咯”地笑,“是这样吗,泰瑞?”
“是的。”泰瑞说。
“听起来不错!”沃克先生说。他们沿着大路开去,穿过村庄的街道,这时弥撒刚刚结束。泰瑞身体左右摇摆,向所有认识的人大声叫喊。大家先是吃了一惊,然后笑了起来,向他挥手。泰瑞继续大声喊,但是,他的声音已经淹没在嘈杂声和车流中了。“比利!比利!”看到比利·格雷出现在教堂外的时候,他尖叫起来。“这是我阿姨的车,我们要去兜风,我有铲子和铁锹。”此刻,佛罗里正站在邮局外,手放在背后。一心想炫耀的泰瑞,特地朝佛罗里喊了一声,阿姨探出车窗,伸出手打招呼。佛罗里抬起头看了一下,假装没认出他们。佛罗里又是这样,她甚至也嫉妒这辆车!
泰瑞之前没有见过大海,这个地方看起来很不一样,于是,他认为这可能就是英国。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风有点大。沿着海滩是一排粉刷成白色的房子。阿姨帮他把衣服脱掉,给他穿上鲜艳的蓝色游泳裤。但是,当海风吹过来,他开始打哆嗦,发出呜咽声,他把两只手放到腋窝下绝望地抱紧自己。
“哎呀,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阿姨故作为难地说。
她和沃克先生也换上了衣服,他们拉起他的手,走到水边。害怕和担心消失了,他坐在浅水区,让明亮的波浪拍打着滑溜溜、圆鼓鼓的肚皮。海水看起来像极了柠檬水,他忍不住尝了一口,但味道是咸的。他想如果这是英国,这儿还不错。尽管他更希望这里有公园和自行车。其他孩子正在堆沙土城堡,于是他决定也堆一个。过了一会儿,令他感到厌烦的是,沃克先生走过来帮忙。泰瑞不明白,这里这么多沙子,他为什么不走开,堆他自己的城堡。
“现在,我们要堆一个大门,对吗?”沃克先生多管闲事地问。
“好,好,好,”泰瑞厌恶地说,“现在,你去那边玩。”
“难道你不喜欢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爸爸吗,泰瑞?”沃克先生突然问。
“我不知道,”泰瑞回答,“我要问问阿姨。门在这里。”
“我想你会喜欢我住的地方,”沃克先生说,“比这里漂亮得多。”
“是吗?”泰瑞感兴趣地问,“什么样的地方?”
“哦,你知道——有旋转木马和秋千,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有公园吗?”泰瑞问。
“是的,有公园。”
“我们现在就去那里吗?”泰瑞急切地问。
“好吧,我们今天不能去,没有船我们去不了。你看,那是英国,就在这一片海水的另一边。”
“你就是那个要和阿姨结婚的男人吗?”泰瑞问,他目瞪口呆,以至于失去平衡,摔了一跤。
“噢,谁告诉你我要和阿姨结婚的?”沃克先生问,似乎也很惊讶。
“她说的。”泰瑞说。
“她真是这么说的吗?天啊。”沃克先生笑着大声说,“好吧,我觉得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包括你在内。她还跟你说了什么?”
“她还说你会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泰瑞着急地说,“你会吗?”
“当然会。”沃克先生认真地说,“首先你得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才会给你买,成交?”
“一言为定。”泰瑞说。
“握手。”沃克先生说,伸出他的手。
“握手。”泰瑞回答,往自己的手里吐口唾沫。
他对沃克先生要成为他父亲这个想法非常满意。他相信沃克先生会是一个好父亲。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他们在海滩上喝茶,回到车站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站台上的小夜灯发出一点亮光。山谷的另一边,高山在黑暗树林的笼罩下,变得朦朦胧胧,没有灯光,一点儿也看不到格雷家小屋的位置。泰瑞很累,不想下车,他开始抱怨起来。
“快一点,泰瑞。”阿姨轻快地说,同时把他从车里拉出来,“跟沃克先生说晚安。”
泰瑞站在沃克先生前面,沃克先生已经下车了,低着头。
“难道你不和我说晚安吗,哥们儿?”沃克先生吃惊地问。
泰瑞抬头看他,感受到他声音里的责备,不顾一切地扑向他的膝盖,把脸埋进他的裤腿里。沃克先生笑了笑,拍了拍泰瑞的肩膀。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高兴一点,泰瑞。”他说,“我们会有很多快乐的时光。”
“快点,泰瑞。”阿姨用十分正式的语气,快速地说,这使他感到害怕。
“怎么了,哥们儿?”沃克先生问。
“我想和你在一起。”泰瑞轻声说,开始抽泣起来,“我不想待在这里,我想和你一起回英国。”
“想和我一起回英国,是吗?”沃克先生重复道,“好吧,今晚我们不能回英国。泰瑞,但是,如果你乖乖地问问阿姨,我们改天再商量这件事。”
“给小孩子说这么多是没有用的。”阿姨说,声音变得尖锐。
“你似乎已经这样做了,做得还不错。”沃克先生安静地说,“所以,你看,我们今晚到不了英国,我们只能改天再去。现在,你先和阿姨一起走。”
“不,不,不。”泰瑞尖叫起来,试图躲开阿姨的胳膊,“她只想摆脱我。”
“好了,是谁告诉你这么邪恶、荒唐的事,泰瑞?”沃克先生严厉地问。
“这是真的,是真的。”泰瑞说,“她不是我阿姨,她是我妈妈。”
话音刚落,他就知道情况变得糟糕透了。这是佛罗里·克兰西说的,她恨他阿姨。从另外两个人的沉默中,他明白了更多。阿姨低头看他,她的眼神让他感到恐惧。
“泰瑞。”她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不要再说些荒唐的话了。”
“让他跟着我吧。”沃克先生不客气地说,“我会找到地方的。”
她同意了。泰瑞马上不再乱踢,不再抱怨,他缓慢地向前靠近沃克先生的肩膀。他知道,这个英国男人站在他这边。此外,他太累了,已经快睡着了。当他听到沃克先生的脚步踏上木桥的厚木板时,他抬起头,看到灰暗的小山丘,覆盖着松树,小河像是天空最后一抹亮光下的铅皮。他再次醒来时,已经到了他和比利一起住的黑暗的小房间。他坐在沃克先生的膝盖上,沃克先生正在给他脱鞋。
“我的铲子。”他叹了口气。
“哦,我向上帝发誓,小伙子。”沃克先生说,“我差点儿把你的铲子给忘了。”
四
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天,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泰瑞总是不自觉地穿过人行桥和火车站,来到大路上。这里有一个酒馆,很多从山谷那边来的男人围坐在墙外,等待四下无人时便溜进去喝一杯。泰瑞把铲子和铁锹也带上了,以防有任何情况他来不及带上它们。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些东西。他坐在墙角下,离那些男人很近,这样他就能看到从公路两边开过来的公车和汽车。有时候,一辆像极了沃克先生的灰色汽车出现在拐角处,他踉踉跄跄地朝它跑去,但是,开车的司机总是让泰瑞感到失望。每当夜晚来临,最早出发的一批公车开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小屋。格雷夫人责备他怎么这样闷闷不乐,哭丧着脸。他也很自责,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对阿姨的承诺。
一个星期天,佛罗里从乡下来到这条大路上。她慢慢地从他身边经过,等着他先说话,可是他没有。这都是她的错,全怪她。于是,她停下脚步,转过身,跟他说起来。她非常清楚他会在这里,她来这里看他是想要做一些补偿。
“你在等谁吗,泰瑞?”她问。
“不关你的事。”泰瑞粗鲁地回答。
“如果你是在等你阿姨的话,她不会来了。”佛罗里继续轻声地说。
在别的情况下,泰瑞不会搭理她,但是现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不管是谁,只要能告诉他阿姨和沃克先生为什么不来,他都愿意听。年仅五岁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任何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问。
“克兰西夫人说的。”佛罗里确信地说,“克兰西夫人知道所有的事情。这些都是她在邮局听到的。开灰色汽车的男人也不会再来了,他已经回英国了。”
泰瑞开始轻声哭泣,他一直担心沃克先生只是在开玩笑。佛罗里慢慢靠近他,坐在他身边的草地上。她拔了一根草秆,把它放在大腿上一条条地撕下来。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她责怪道,“你知道,我一直都是你的女朋友,我不会跟你说谎的。”
“但是为什么沃克先生回英国了?”他问。
“因为你阿姨不能跟他一起去。”
“她说她会的。”
“她母亲不会让她走的,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如果她跟他走了,他也会把你带走。他没有这么做,你应该感到幸运。”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新教徒。”佛罗里一本正经地说,“新教徒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正派的教徒。”
泰瑞竭尽所能想要弄清楚,对于一个人来说,一个所谓正派的宗教信仰怎么能够弥补一个电灯可以随时开关的大房子、一个公园和一辆自行车的损失,但是他意识到自己还太小。对于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孩,这些太深奥了。
“但是,为什么阿姨不再像以前那样来看我了?”
“因为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喜欢她来看你。”
“他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这是不对的。”佛罗里用充满同情、怜悯的语气回答,“难道你不明白那个英国男人没有宗教信仰,因此,他不介意。但是,你阿姨嫁的那个人是她工作店铺的老板。克兰西夫人说‘他会娶她,让人感到吃惊。’他不喜欢她来这里看你。她以后会有合法的孩子,你明白吗?”
“难道我们不是合法的孩子吗?”
“噢,不,我们不是。”佛罗里沮丧地说。
“那我们做错什么了?”
佛罗里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她太骄傲了,不想让泰瑞这样的小男孩知道,她根本不知道答案。
“一切都是错的。”她叹了口气。
“佛罗里·克兰西。”酒馆外面一个男人大声喊,“你对那个小孩做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她回答,语气有些恼怒,仿佛被人从梦中吵醒一样,“你不应该一个人在这里,他会跑过来。现在,跟我一起回家吧,泰瑞。”她又说,牵住他的手。
“她说过会带我去英国,给我买一辆属于我自己的自行车。”他们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泰瑞号啕大哭起来。
“她只是在骗你。”佛罗里自以为是地说,她的语气慢慢发生了变化,变得充满嘲讽,“当她有了其他孩子,她就会忘记关于你的一切。克兰西夫人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她说没有人值得你伤心,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人,只考虑自己。她还说我父亲有一大笔钱。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等你长大一点儿,我就会嫁给你。”
她带他走小路,穿过这片树林。树木变成各种颜色。一会儿,她坐在草地上,安静地抚平垂到膝盖的裙子。
“你哭什么?”她责备地问,“这全都是你的错。我一直都是你的女朋友,不管格雷夫人说什么,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我一直站在你这边。我不想看到你被那个女人和她的承诺欺骗,可是你没有把我当一回事,只把她和她给你的玩具当成宝贝。我告诉过你她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你不相信我。好了,现在看看你自己。如果你发誓会永远和我在一起,我还是你的女朋友。你会吗?”
“我会的。”泰瑞说。
她把他抱在怀里,他睡着了,但是,她仍然认真地抱着他,用冷静、好奇的眼神注视着他。他最终还是属于她的,不会再有其他对手。她也睡着了,不知道火车已经爬上山谷。所有的灯都点亮了,夜晚已经降临。
一家之主
作为一个小孩子,如果我能集中注意力的话,我就会表现得很好。精神集中一直是我的弱点,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旦我将注意力从我正在做的事情上转移,我就会茫然不知所措。
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晨我是怎么醒来的,然后,我听到楼下厨房里传来奇怪的咳嗽声。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哪里不对劲。我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她正歪着身子坐在壁炉前的一把小藤椅上。她试着把火点着,但是,炉火总是跟她作对。
“怎么了,妈妈?”我问。
“这些柴火是湿的,火苗呛得我咳嗽了,”她说,还试着冲我笑一下,虽然,我看得出来她已经痛得直不起腰来。
“我来生火,你去床上躺着吧。”我说。
“哦,我怎么能?孩子,”她说,“当然,我得去上班。”
“你病成这样不能去上班,”我说,“去床上躺着吧,我会把你的早饭端过来的。”
女人真是可笑,尤其是她们听从男人指挥的样子,即使是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
“如果你能为自己烧一杯茶,我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好了。”她一边说一边虚弱地拖着脚步走上楼去。我和她一起上楼,撑着她的胳膊,她一到床边就晕倒了。那时,我才知道她肯定很不舒服。我拿了更多的柴火——她总是那么节省,每次生火的时候都用得不够多。我一会儿就让炉火烧得很旺,然后,我把水壶放在炉火上。我也给她做了烤面包片,我对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片的好味道深信不疑。
我想她相当疑惑地看着那杯茶。
“茶还可以吗?”我问。
“你没有剩下一点儿开水吗?”她问。
“茶太浓了,”我表示同意,同时,我试图消除我声音里一丝失望的痕迹,“我会倒掉一半。我永远都记不住怎么做。”
“但愿你上学不会迟到。”她焦急地说。
“我不去上学了,”我说,“我现在就去拿你的茶,然后,我帮你跑腿做事情。”
关于我不去上学的事情,她什么也没有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她需要的就是听从指挥。我把早饭的餐具洗刷干净,然后,我自己洗漱好,我拿着购物篮子,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来到她身边。
“如果你都写下来,我来帮你做,”我说,“我猜我要先去找斯莱特里夫人,是吗?”
“告诉她我明天一定会来。”
“把斯莱特里夫人写下来,”我坚定地说,“我要去找医生吗?”
“实际上,你不用去找医生,”母亲担心地说,“他只想把我送到医院去。他们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让药师给你一瓶强力止咳药水。”
“写下来,”我说,记得我自己的弱点,“如果没有写下来,我可能会忘记的。而且,把‘强力’这个单词用大写字母来写。晚饭我买点什么呢?鸡蛋吗?”
那真的是有点儿吹牛了,因为,我会做的饭就是鸡蛋,但是,母亲让我买些香肠回来,万一她能起床就可以做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先去拜访斯莱特里夫人,我母亲为她工作,我告诉她我母亲今天不能来上班。我不太喜欢斯莱特里夫人。她的脸又大又宽,这样的脸型需要宽大的五官才相称,但是,她的脸上却是咪咪的小眼睛和又瘦又尖的鼻子,这些五官似乎都消失在宽阔的脸上了。
“她说她尽量明天过来上班,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让她起床。”我说。
“如果她的病没有好,我不会让她回来的,格斯,”她说,而且,她给了我一便士。
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心里备受鼓舞。我早就知道一个人总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如果他能勇敢地面对,那么,他也会从中得到好处呢。就拿学校来说吧。我站在学校对面盯着看了足足有十分钟。校舍和倾斜的院子像是一幅画,除了从敞开的窗户传来那些可怜的受难者一起读书的声音。我瞥了一眼丹尼·德莱尼的光头,当他像哨兵一样迈着步子走过前门,他拿的藤条就像尾巴一样在他身后晃来晃去。我和商店里的伙计聊起天来,我告诉他们母亲的咳嗽说不定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把情况说得更糟糕一些是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动听,但是,我私底下还是希望我回到家的时候她的病已经好了,这样,她就能用香肠做晚饭了。我讨厌煮鸡蛋,而且,无论如何,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承担责任的压力了。
然而,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明妮·赖安和她在一起。明妮是一个中年妇女,喜欢闲聊,有些虚伪,却消息灵通。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妈妈?”我问。
“我好多了。”她笑着说。
“虽然,她今天还不能下床。”明妮坚定地说。
“我一会儿就给你倒你的咳嗽药水,然后,我再给你拿杯茶过来,”我说,隐藏了心中的失望。
“哎呀,我来做吧,孩子。”明妮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
“哦,你不用介意,赖安小姐,”我毫不慌乱地说,“我能够做好。”
“他不是很棒吗?”当我下楼的时候,我听到她小声地赞叹道。
“明妮,”我母亲低声说,“他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养育的最好的孩子。”
“为什么,话说回来,很少有孩子能像他这样,”明妮沮丧地说。“你看现在大多数孩子更像是野蛮人而不是基督徒。”
下午,我母亲想让我出去玩,但是,我不会走得太远。我记得我自己的弱点。我知道一旦我走出一定的距离,我应该会慢慢地晃到格伦河谷,兵营的训练场就坐落在格伦河谷的悬崖峭壁之上;河谷下面就是步枪射击场,再往下走就是磨坊贮水池和从树木茂盛的峡谷穿流而过的磨坊小河——落基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或者海兰兹山地,根据你的心情来定。精神集中——这是我不得不练习的事情。一不留心,我应该就会和那些明妮·赖安不赞同的孩子们混在一起了,他们更像是野蛮人而不是基督徒。
夜晚来临,街上的煤油灯已经点亮,卖报的小孩沿着马路大声地叫卖。我买了一份报纸,点着了厨房里的煤油灯和卧室里的蜡烛,然后,我给我母亲读那些警察、法院的新闻。我知道她最喜欢这样的新闻,全都是关于人们喝醉酒在航道被抓捕的消息。我读的不是很快,因为,我只会念一个音节的单词,然而,她似乎并不介意。
后来,明妮又来了,她走的时候,我把她送到门口。她看起来表情严肃。
“如果她明天早晨还是没有好一点儿的话,我想我会给她叫医生的,格斯。”她说。
“为什么?”我警觉地问,“你是说她病得更严重了吗?”
“哦,不,”她说,用力地拽了一下她的旧披肩,“只是我被从前的肺炎吓坏了。”
“但是,他不会送她去医院吗,赖安小姐?”
“哦,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不管怎样,他能给她开点好的药水。但是,即使他这么做,上帝在我们和所有的伤害之间,这不是比没有人照看好多了吗?如果你有一些威士忌,你可以把威士忌加热,再榨一点儿柠檬放进去给她喝。”
“我一会儿就去买。”我立即说。
母亲不想喝威士忌,她说威士忌太贵了。但是,我知道威士忌与住院和其他费用比起来便宜得多,所以,我不会听她的。
我之前从来没有去过小酒馆,里面拥挤的人群让我害怕。
“哈啰,我的老朋友,”一个高个子男人说,他一脸坏相地冲我咧嘴一笑,“自从我上次见到你快有十年了吧。等一下——你不是在南非吗?”
我的朋友,鲍勃·康奈利,曾经跟我吹嘘说他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要半克朗,那个人居然给他了。我一直都想鼓起勇气做同样的事,但是,即使在那时,我还是不敢。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想给我母亲买半杯威士忌。”
“哦,你这个讨厌的坏蛋!”那个人一边说一边拍着手,“假装是买给你母亲,他是开普敦城镇最臭名昭著的醉汉。”
“我不是。”我说,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而且,是给我母亲买的,她生病了。”
“放开那个孩子,约翰,”酒吧女服务员说,“你没有听见他说他母亲生病了吗?”
母亲喝完热的威士忌之后就睡着了,然而,我却不能休息。我在想小酒馆里的那个人是怎么认为我在南非的,而且,我有点儿责怪自己没有跟他要半克朗。如果妈妈真的生病了,半克朗迟早会派上用场的。当我真正睡着的时候,我又被她的咳嗽声吵醒。我走进卧室的时候,她正在说胡话。她已经不认得我了,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我害怕。
第二天早晨,虽然喝了威士忌,她还是不见好,这种失望感真的是很糟糕。我把早饭拿给她之后就去见明妮·赖安。
“我得马上去找医生。”她说,“你出去的时候,我会陪着她的。”
要去找医生,我得先去一个殡仪业工作人员家里,他是济贫法的维护者,我要从他那里拿个单子证明我们付不起医药费,然后,我要去诊所。接下来,我得快点跑回来,把房间整理一下,给医生准备好一盆水、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让他洗手用。
我们吃完晚饭后他才来。他是一个身形肥胖、动作缓慢、声音洪亮的人,有一撇灰白色的小胡子,而且,像医药行业里所有的醉汉一样,他应该是“科克市最聪明的人,只要他留心自己的形象。”从他那天早晨的穿着打扮来看,他并没有过多在意自己的形象。
“你现在要怎么去拿药?”他一边生气地说,一边在床边坐下来,把开处方的垫本放在膝盖上,“只有北部药房还开着门。”
“我去,医生。”我立即说。
“那里很远,”他怀疑地说,“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会找到的。”我自信地说。
“难道他不是一个很棒的帮手吗?”他对母亲说。
“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她叹了口气,盯着我看了很久,“一个女儿也不可能比他更好。”
“说得对。”他对我说。“你能做到的时候要照看好你的母亲。归根到底,她是对你最好的人……当我们拥有她们的时候,我们并不在意,”他对母亲补充道,“而我们却用下半生的时间悔恨我们没有在意她们。”
我自己不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因为,我费了这么大劲,他根本就没有洗手,然而,既然他没有提到医院,我打算忽略这一点。
去药房的路要往山上走,穿过一片人口密集的穷人居住区,这条路和坐落在山顶的兵营一样远。然后,这条路一直向下倾斜,穿行在高墙之间,直到几乎突然消失在山坡那边。然后,有一条石头小路出现,小路右侧是一排红砖砌成的公司厂房,另外一侧穿过一片宽阔的空地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令人震惊的景象。这个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剧院的背景幕布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镇。小路形成一个陡峭的斜坡,斜坡延伸到一条小河的河岸,河边有一个啤酒厂。从这个位置,在你脚下很远的地方,在对面的山坡上,工厂的烟囱和厂房像蜂巢一样发出嗡嗡的响声,这些响声传到你的耳边,支离破碎、幽灵一般。这些烟囱和厂房陡直地向上,陡直地耸立在坡度平缓地环绕的山顶。每一座建筑都有一个石灰岩的尖顶,一座紫色的砂岩高塔矗立在其中,高耸入云。这个景象是如此的广阔和让人晕眩,以至于从来没有人同时将这些景色尽收眼底。阳光悠闲地照过山坡,就像是照过一片草原,一排像雪一样明亮的屋顶清晰可见,或者,光线照进某一条黑暗街道的深处,在阴影中显现出正在爬行的马车和拼尽全力拉车的马匹的轮廓。我感到兴奋不已,就像是一个旅客,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我下定决心把斯莱特里夫人给我的一便士用来买一根蜡烛,送给山顶教堂中安置的圣母玛利亚,祈求我母亲的病快一点儿好起来。我确信在一个这么接近天堂的,伟大的教堂里,我做的事会更有价值。
药房在一个脏乱不堪的大厅,大厅的一边有一张长凳,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像铁路售票窗口一样的窗户。一个肩膀上围着一条绿色毛呢料长披肩的小姑娘坐在凳子上。她匆匆地看了我一眼,而我看到她的眼睛也是绿色的。多年以后,每当有女孩子像那样急匆匆地看我时,我躲闪着。我知道那眼神意味着什么,然而,当时我还很天真。我敲了敲窗户,一个穿着破烂衣服,一脸怒气的人打开窗户。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抓起瓶子和药方,“砰”的一声又关上百叶窗,他一个字也没有说。我等了一分钟,然后,我又举起手来敲第二次。
“你要等一下,小男生。”那个女孩很快地说。
“我为什么要等一下?”我问。
“他要配药,”她解释道,“他可能要用半个小时。你可能也要坐下来等。”
因为她显然很了解情况,我就按照她说的做了。
“你从哪里来的?”她继续问,她把披肩拿下来放到嘴巴前面,我曾经看到一些妇女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我住在布拉尼巷。”
“我住在兵营附近。”我说。
“那么,那瓶药水是给谁的?”她问。
“我妈妈。”
“她哪里不舒服吗?”
“她咳嗽得很厉害。”
“她可能患了肺结核,”这个小姑娘开心地说,“我姐姐去年就是患上肺结核死的。我另外一个姐姐不得不吃补药。这就是我正在等着拿的药。这真是一个古怪的旧世界。你住的地方好玩吗?”
我告诉她关于格伦河谷的事情,她跟我说了汇入卡里罗海恩的河流。从她描述的样子来看,那似乎是一个比我们这里更棒的地方。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爱说话的小姑娘,而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突然,百叶窗被推上去,一瓶药水被“砰”的一声放在柜台上。
“杜丽!”那个人说,窗户又被关上了。
“那是我,”那个小姑娘说,“我的名字是诺拉·杜丽。你的药还要等很久才会配好。你的药是红色还是黑色?”
“我不知道,”我说,“我之前没有来买过药。”
“黑色的更好喝,”她说,“红色的药水更多的是配给很严重的咳嗽。然而,我现在倒是不介意一瓶红色的。”
“我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我说,“我有钱买糖吃。”
毕竟,我已经决定我没有必要去点一根蜡烛。这个小姑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恢复了我的自信。我知道我把情况夸大了,母亲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我拿到的瓶子是黑色的。这个小姑娘和我坐在医务室的台阶上吃我刚刚买来的糖果。巷子尽头是山顿的石灰岩尖顶;沿着一路都是晒得热烘烘的高墙和墙上的一排小树,这时,太阳出来了,金色的热浪就在我们身后,在马路上映出我们连在一起的身影。
“我们尝尝你的药水吧,小男生。”她说。
“你不能尝你自己的吗?”我怀疑地回答。
“哦,你不能喝我的,”她说,“补药都很难喝。尝尝吧!”
我尝了一口,很快就吐出来了。真是难喝。然而,我尝过她的之后我就不能不让她尝一下我的。她喝了一大口,这使我很担心。
“太好喝了,”她说,“那就像我姐姐去年死的时候经常喝的一样。我喜欢喝咳嗽药水。”
我自己尝了一口,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觉她说的不错。药水很甜,很黏稠,有点儿像糖饴。
“我们再喝一口吧。”她说。
“我不要,”我警惕地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要做的就是用水泵把水倒进去。没有人会发现的。”
不知怎的,我总不能拒绝她。母亲离我那么远,而我被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停泊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这里有尖顶、塔楼、树木、楼梯,还有喜欢喝咳嗽药水的小姑娘。我崇拜着那个小姑娘。我们两个都喝了第二口,而我心里开始发慌。我看得出来即使你把水倒进去,你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开始伤心地哭起来。
“药水都没有了,”我说,“我要怎么办?”
“喝掉它,就说瓶塞掉下来了。”她说,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上帝原谅我,我相信了她说的话。我们把药水喝完,然后,当我收起空瓶子的时候,我记起我母亲还在生病,而且,我冒犯了圣母玛利亚,我感到失望。我为了一个甚至都不关心我的小姑娘牺牲了她们。从我一开始出现在药房的时候,她一直想要的都是我的咳嗽药水。我看穿了她的欺诈行为,开始抽泣起来。
“你怎么啦?”她吃惊地问。
“我妈妈生病了,而你跟着我喝了她的药水,如果她现在死了,都是我的错。”我说。
“哦,别像个哭鼻子的婴儿!”她轻蔑地说,“没有人是死于咳嗽的。你只需要说瓶塞掉下来了——任何人都会碰上这种事。”
“我还跟圣母玛利亚承诺过要买一根蜡烛,我把买蜡烛的钱给你买糖吃了。”我大声说,像疯子一样跑到马路上去,手里拿着空的药瓶。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一个奇迹。我来到教堂里圣母玛利亚的神龛前面,告诉她我的堕落行为,跟她保证我下次拿到一便士就给她买蜡烛,只要她让我回到家的时候能看到母亲好一些。我在烛光中认真地看着她的脸,觉得她看起来不太生气。然后,我心情痛苦地回到家。白天所有的光线都消失不见了,发出回声的山坡已经变成一个广阔的、怪异的、残酷的世界。此外,我感觉到自己病得很厉害。我甚至觉得我自己可能要死了。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倒是一个很大的解脱。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厨房里一片寂静,我看到壁炉旁边没有人,我立即明白圣母玛利亚没有听到我的祈祷。母亲仍然躺在床上病着。我开始号啕大哭。
“究竟怎么了,孩子?”她从楼上焦急地大声喊道。
“我把药水弄丢了。”我从楼梯底下痛苦地大声说。然后,我不顾一切地冲上楼,把我的脸埋到床单里。
“哦,哎呀,哎呀,如果这就是惹你的麻烦事,你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她大声说,同时松了口气,她的手抚弄着我的头发,“我害怕你迷路了。出什么事了?”她焦急地说,“你身上发热了。”
“我喝了药水,”我大声说,又把头埋到床单里去。
“那么,如果你自己喝了,又有什么坏处呢?”她安慰地低声说。“你这个可怜的孩子,自己一个人走过去,没有吃饭,也没有吃别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呢?现在,把衣服脱下来,躺在这儿,直到你觉得好受一点儿。”
她站起身,穿上她的拖鞋和外套,然后,我坐在床上,她给我解开鞋带。她还没等收拾好我已经睡着了。我没有听见她穿上衣服或者走出去,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我的额头上有一只冷冰冰的手,我看到明妮正低头盯着我。
“哦,没什么,老朋友。”她轻快地说,“他睡一觉明天一早就没事了。嗯,他们难道不是恶魔吗!天晓得,你根本不能指望他们。确实如此,确实如此。苏里文夫人,你才应该躺在床上休息。”
我知道这一切,我知道这就是她对我的评价;我就是那些更像野蛮人而不是基督徒的家伙中的一个;我不是一个好的看护,我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我接受这一切。但是,当母亲拿着她的晚报,坐在我的床边读报纸的时候,我知道奇迹已经发生了。她的病已经治好了。
醉 汉
住在排屋的杜利先生去世了,这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杜利先生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他的两个儿子是道明会的成员,他自己拥有一辆汽车。他的社会地位可比我们高得多,但是,他却没有妄自尊大。杜利先生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像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与人攀谈。父亲以他自己有限的方式读了很多书,而且,他能够欣赏说话机智、聪明的人。杜利先生是一个非常机智、聪明的人。从商业相识到神职人员,镇上很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且,每天晚上,他会穿过马路来到我们家门口,给父亲解释新闻背后的故事。他的声音低沉、说起话来夸夸其谈,他的脸上有一种洞察世事的笑容,而且,父亲会吃惊地听着,还时不时说些话来引导他,然后,父亲会得意洋洋地跺着脚来到母亲面前,满面红光地问:“你知道杜利先生告诉我什么吗?”从那以后,每当有人私下里跟我说一些小道消息,我发现自己都会马上问道:“是杜利先生告诉你的吗?”
我没有把他去世的消息当真,直到我真的看到有人把他的尸体入殓,他身上穿着褐色的裹尸布,玫瑰念珠缠绕在他那苍白、光滑的手指上。即使在那时,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在某个夏天的夜晚,杜利先生一定会再次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给我们讲述另外一个世界的内幕消息。但是,父亲却非常沮丧,或许是由于杜利先生和他自己年纪相仿,这种事情总是会对另外一个人的死亡带来明显的个体的转变。或许是由于现在没有人来告诉他最近市政委员会事件背后的苦差事。你掰着指头也能数得过来,在布拉尼巷有几个人像杜利先生那样读报纸,而且,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忽略父亲仅仅是一个工人的事实。甚至是苏里文,那个木匠,一个无名小卒,他认为他比父亲高一等。这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两点半去卡拉沼泽地。”父亲若有所思地说,他放下手中的报纸。
“但是,你不是想着要去参加葬礼吧?”母亲惊慌地问。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父亲说,他察觉出母亲的反对,“我不会和他们说的。”
“我认为,”母亲压抑着情感说,“如果你能陪着他去教堂,大家都会很乐意的。”
“去教堂”,当然,是另一回事,因为,遗体是在人们下班后才被挪动,但是,去参加葬礼则意味着少挣半天的工钱。
“那些人几乎都不认识我们。”她补充道。
“上帝在我们和所有的伤害之间,”父亲极有尊严地回答,“如果事情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我们会很高兴的。”
平心而论,父亲总是随时准备为了某个老邻居而耽误半天的工夫。这并不是由于他有多么喜欢葬礼,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的人,他会按照人们将来对待他的方式来做事情。而且,没有什么比他想到自己去世后将会有一场令人称道的葬礼更能宽慰他的了。那么,平心而论,母亲并不是吝惜半天的工钱,尽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负担不起。
喝酒,你是知道的,是父亲的一大弱点。他能连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保持冷静、滴酒不沾,而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会表现得非常好。早晨,他第一个起床,端着一杯茶去卧室给母亲;晚上,他会待在家里读报纸;他会攒钱,给他自己买一套新的蓝色哔叽西服和一顶圆顶硬礼帽。他会嘲笑接连好多个星期把他们辛苦挣的钱留给酒馆老板的那些人的愚蠢行为。而且,有时候,为了打发一个小时的闲暇,他会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准确地计算出成为一个滴酒不沾的人,每个星期他能节省多少钱。作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有时候会一直计算到他预期寿命的这些年他能够攒下多少钱,这笔钱的数目可是激动人心的。他去世的时候会有好几百英镑呢。
要是我早就知道的话,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这预示着精神上的骄傲填充了他的内心,他想象着自己比他的邻居们过得更好。早晚有一天,这种精神上的骄傲越积越多,直到他想要庆祝一下。然后,他会喝上一杯——不是威士忌,当然,完全不是那种酒——只是一杯无关紧要的啤酒。父亲对滴酒不沾的坚守也到此结束。他喝了第一杯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他让自己出洋相了。然后,他再去喝第二杯来忘记这件事,再去喝第三杯来忘记他不能忘记的事实,最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从这时开始,我们会见识到“醉汉的历程”,正如在一些道德作品中写的那样。第二天,他头疼得厉害,待在家里不能干活,这时,母亲要跑去他干活的地方帮他找借口请假;而且,两个星期之内,他又变得贫穷、野蛮、意志消沉。一旦他开始喝起酒来,他会把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厨房里的时钟,都拿去喝掉。母亲和我知道所有的这些阶段,我们害怕所有让他喝酒的危险信号。葬礼就是一个。
“我得去邓菲家做半天的工,”母亲忧虑不安地说,“谁来照顾拉里?”
“我来照顾拉里,”父亲殷勤地说,“走一点路对他有好处。”
不用多说什么了,尽管我们都知道我根本不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